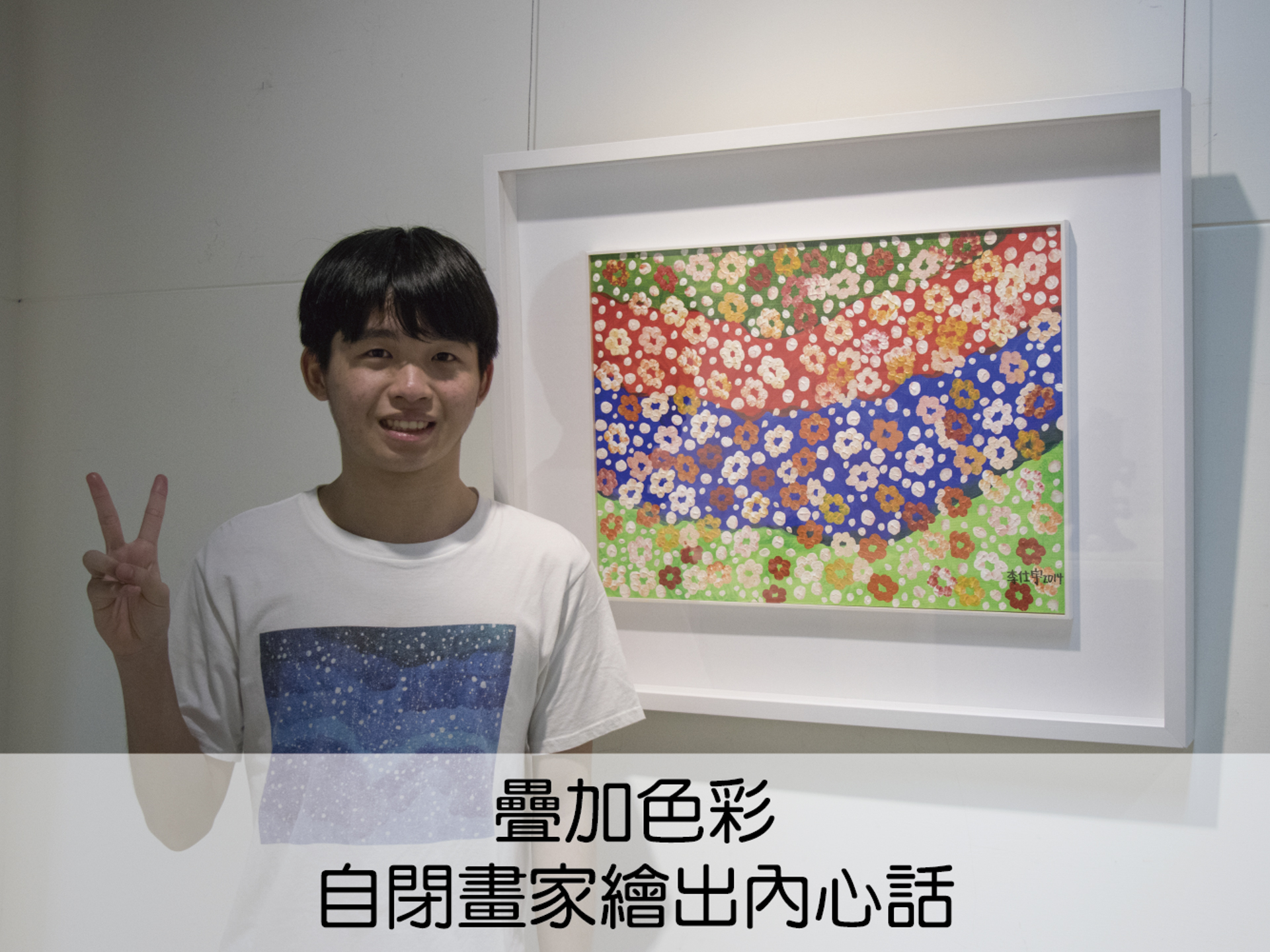.jpg)
林莉庭
2019/4/11
【專題記者林莉庭、徐卉馨、吳佩容、范莛威綜合報導】輪椅上的身影脫離家庭與安置機構,選擇融入社會生活,穿梭在大街小巷、編織自身的人際網絡。在社會中自立生活是許多身障者理想的生活方式,但仍不乏遺落在社區網絡外的身障者,離開家人的呵護或機構安排的環境,舉目望見許多待解決的難題。
多數人對身障者的印象是生活於機構或由家人照顧的樣貌,但其實他們非常渴望與社會互動,因此整篇專題的開頭,希望能追溯身障者遇到居住權困境的根本原因,便是盼望自立生活的需求,建立在這個基礎上,接著往下延伸發掘身障者於租屋時會遇上建築結構、租金過高、旁人目光等問題。
「在機構裡面,你的人會慢慢死去……」
「這個空間的理念就是要讓身障者在社區生活,實驗障礙者互助的概念。」異於常人算障社會推動工作聯盟(以下簡稱算障團)身障者周志文表示,混障家屋是算障團成員承租並共同生活的家屋,同住的身障者在社區中彼此守望互助。客廳空間足夠讓多位乘坐輪椅的身障者活動,周志文也在混障家屋中舉辦過地板滾球、桌遊等社交活動。
周志文坦言,政府雖為身障者提供集中照護的機構,但機構人力不足以提供每位居住者妥善照顧,加上身障者接受特別安置、統一管理,易加深身障者與社會的隔閡。他提及創辦混障家屋的動機,「我們要回應我們自己,自己的障礙政策要自己先落實。」唯有身障者回歸社會網絡,居住於社區中,才得以漸漸化解社會對身障者的不理解,不再被視為特殊的存在。

算障團的周志文,一面描述看房的情形,一面傾訴大環境為身障者帶來的不便。 圖/范莛威攝有別於原生家庭和安置機構,混障家屋提供身障者一種可能的生活圖像——自立生活。與家人同住,對身障者而言甜蜜與苦澀並存,享有家人的關照,卻也不願自己成為親情的負擔。財團法人台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(以下簡稱脊損基金會)副執行長洪心平說:「我想很多身障者有家人當然很幸福,但是因為跟照顧者之間的關係,會是一種拉扯。」他曾接觸過在國小期間受傷的身障者,隨年紀成長開始嚮往獨立居住,規劃理想的生活模式。
與自身經驗聯想,大約在大學時便會嚮往在外居住、自行安排生活,身障者也不例外,只是他們在邁向理想生活模式的路上,會遇上更多難關,像是要更花心思與家人溝通,因為家人不免會擔心他們的自理能力,而實際自立生活後,也會遇上租屋、求職等挑戰。洪心平認為,家人盡力照顧身障者可能造成過度保護的情況,會讓身障者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,或是沒有動力積極做復健,久了體能衰弱、肌肉軟化,連受傷部位以外的地方也失去活動能力。身障者陳青琪也建議,若身障者願意求職也順利穩定就業,將能協助減輕家庭的負擔。
至於身障者在安置機構的生活環境,洪心平則觀察到,安置機構替每位居住者硬性規劃生活時程,也缺乏個人空間的隱私性,許多身障者希望能脫離機構,便是因為不願再過著被安排好、日復一日的生活。
這部分志文也有跟我聊到,他回想在機構的日子,被侷限在特定的活動範圍內,也須等待照顧者為自己打理飲食、洗澡、翻身等生活細節,久了會失去自理能力,最終可能必須依賴他人才得以維持日常生活,而這是身障者極不願意迎來的結果。社團法人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(以下簡稱新巨輪協會)理事長陳安宗曾至安置機構參觀,他表示出入安置中心需要經過申請程序,待在機構內的身障者也多半依靠政府補助,他說:「在裡面沒有收入、沒有工作,幾乎就是被圈養。」長年待在機構中使身障者無法經濟獨立,便缺乏規劃自身生活的資本。
經歷八年機構生活的身障者張文豪回憶道,曾住的機構一個位於海邊、一個鄰近工廠,地處偏僻。身障者亦須配合機構規定,不能隨意外出,絕少有與社會大眾接觸的機會。「在機構裡面你的人會慢慢死掉,因為他生活很死。」張文豪以三年時間慢慢計畫離開機構,如今已在外自立生活兩年,可以自由安排生活、與社會接觸,他說:「因為有生活壓力,人才會過的比較充實。」
 張文豪曾居住在機構八年,而目前已外出生活三年,他表示最大的好處是自由。 圖/林莉庭攝
張文豪曾居住在機構八年,而目前已外出生活三年,他表示最大的好處是自由。 圖/林莉庭攝找尋住屋時,身障者所面臨的障礙
身障者自立生活的重要條件便是尋找宜居的住所,但尋覓住處的過程會面臨許多阻礙。周志文說:「光是我親自到現場看的就有三、四十間屋子。」但許多建築入口的電梯前面還有樓梯、大門太小輪椅推不進去、走廊過窄沒有迴轉空間,周志文遇到的困擾,也是許多身障者尋覓住處時的難關。他也回想,曾連進門都沒辦法,便直接放棄,「電梯前有一個很陡的斜坡,一定要別人幫忙推,結果電梯太窄我輪椅進不去,連房子都沒看到就離開了。」
「但有些房子大概的格局是可以的,只是可能要稍微改裝。」周志文解釋,那就要看房東的意願。身障者陳青琪則說:「有些房東就是怕你把房子用壞。」碰到這種房東就直接不租,省得以後被找麻煩。陳青琪在找房子時碰壁多次,部分房東對身障者有一定刻板印象,認為他們比起一般人更具無法負擔房租的風險,身為脊髓損傷者,陳青琪終日需以輪椅代步,而丈夫則是視障者。「在找房子的時候絕對不能帶著我先生,不然不可能成交,更不能帶著我的兩個孩子,那樣成交機會更低。」陳青琪語氣戲謔,卻掩不住心酸的眼神。
 身為脊損基金會的無障礙勘檢員,陳青琪經常替身障者勘查各住所的環境條件。 圖/范莛威攝
身為脊損基金會的無障礙勘檢員,陳青琪經常替身障者勘查各住所的環境條件。 圖/范莛威攝「有時候,會被房東刻意迴避。」林鈺翔無奈笑道,他20歲時因意外造成四肢癱瘓,從那以後他的生活起居皆離不開看護和輪椅,其原先的住所為老舊公寓,沒有電梯,因此他的家人也為了是否應該搬家而困擾,而他在決定自己搬出去後,找房子又成為一大阻礙。林鈺翔需要一間鄰近就職處、看護能夠同住以及整體環境可以讓輪椅暢行的屋子,然而找到後,卻又面臨房東在簽約前突然迴避的情況,林鈺翔解釋,「我們要申請補助,就會需要正式報稅證明,很多房東會不願意。」
被房東迴避是身障者租屋時經常遇到的情況,因為房東會擔心他們繳不出房租,或是需要根據輪椅能活動的空間更改房屋動線,其實會有租房需求的身障者多半有經濟能力可以負擔自己的房租,房東會擔憂加上無障礙設施的房子未來將租不出去,但改動過的房子也可以再租給下一位身障者。只要雙方有機會溝通,很多房東都會願意出租房屋的。 林鈺翔談及看屋經驗,前後看了六、七次,房屋格局皆不適合輪椅使用,輾轉才找到目前的住處。 圖/林莉庭攝
林鈺翔談及看屋經驗,前後看了六、七次,房屋格局皆不適合輪椅使用,輾轉才找到目前的住處。 圖/林莉庭攝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提供身心障礙者申請房屋租金補貼,身障者需提供正式租賃房屋契約的報稅證明,而這需要屋主配合。但台灣目前多數的租屋交易,多在檯面下進行,政府並不一定能夠查到每筆租屋交易,因此在一般的交易情況,房東多會躲避因租屋收入而課徵的綜合所得稅。「若是租給身障者,他們就必須多繳納稅金。」周志文舉例,曾有某位房東雖願意讓他申請租屋補助,但要求他負擔這筆稅金,「那這樣基本上就快2萬8、3萬了,那我就說我們沒辦法,這實在太貴了。」
「身障者需要的是在受傷後回歸原先的生活。」洪心平表示,但當身障者連在家中的生活都有困難時,又該如何談其它?身障者在尋找住宅的過程中,時常無法找到符合輔具行動範圍需求的租屋處,或者房東會刻意迴避,讓他們一次次拖著沉重的身軀,跑遍各個房屋。「其實不是每個房東都不好,只是多數會因為不了解身障者的需求而害怕,因為害怕而不敢幫忙。」
其實害怕的源頭便是不了解,因此會根據自身狹隘的認知去逃避或拒絕接觸,這是身障者在社會經常感到無力的原因,不僅是租屋受挫,舉凡搭乘大眾交通工具、到公共場合活動,都會從人們的眼光中,看見因不理解而流露的不耐。連養家都難,還有錢租房子?
除了與房東交涉時遇到的種種困難,身障者還需面臨租金的問題,租金時常成為身障者在外尋找住屋時,第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,而空間和交通需求都會牽動租金高低。
陳青琪說:「租屋的費用其實我們都比別人高,因為我們要的空間比較大。」身障者因使用輔具,需要坪數較大、格局寬闊的住房空間,走廊轉角和門的寬度也都是考量範圍。陳青琪也指出,身障者出入亦需便捷的交通設施,然而捷運沿線、鄰近公車站牌的房屋,租金相對高昂,「交通方便的地方就是租金貴。」
 陳安宗認為,身障者在新巨輪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間,因此堅持每人一間,略寬的走廊也能夠讓使用輪椅的身障者順利迴轉。 圖/林莉庭攝
陳安宗認為,身障者在新巨輪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間,因此堅持每人一間,略寬的走廊也能夠讓使用輪椅的身障者順利迴轉。 圖/林莉庭攝身障者的經濟能力亦影響租屋選擇,沒有工作的身障者,通常以補助和津貼為主要收入來源,而台北市社會局核發的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,最高金額為每人每月補助8499元。身障者支付生活費開銷之餘,還需負擔高額租金,不易維繫生活。
至於身體狀況尚可工作的身障者,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發布的《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》顯示,身心障礙受僱者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為2萬5939元。陳青琪以街賣工作為例說明,平均一天工作三小時、賺入150元的身障者,加上政府津貼,一個月收入可達約2萬元,「你租個7、8千塊的房子,也還有1萬多塊可以吃飯。」 。」
陳青琪認為,身障者自立生活的基礎必須建立在經濟獨立之上,而非等著接受他人救濟,「雖然說政府要照顧我們,但他要照顧的族群這麼多,什麼時候才輪到你啊!」他鼓勵身障者透過工作賺取收入,唯有確保經濟來源無虞,才能負擔住屋的租金,也才得以邁開自立生活的第一步。
身障者共居,新型態的租屋模式
除在外租屋,身障者也可選擇社會住宅,政府提供或承辦的住宅是身障者積極尋求的居住管道。目前《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》規定,政府新建的公共住宅應保留5%房型加入無障礙設施。然而,各障別的身障者皆可申請上述的無障礙房型,擠壓到需使用輪椅移動的下肢障者名額,對此,洪心平建議將障礙類別再細分,讓輪椅使用者能佔所有無障礙房型名額的固定比例。
針對無障礙房型申請名額的問題,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發展科專員蔡昆達則回覆,適用無障礙房型的族群類別廣泛,但輪椅使用者所需的房型設計較特殊,空間較大、也需加裝扶手,因此會優先開放下肢障者申請無障礙房型。至於舊有的公共住宅,在接收到無障礙設施未臻完善的建議時,因需考量房屋結構,無法一概改動空間設計。
目前社會住宅仍受限於名額,身障者申請不易,接受機構安置,則會讓身障者隔離於社會,在外租屋也常遇到租金和房東等問題,因此,身障者共居便成了另一劑解方。以新巨輪協會為例,協會除提供身障者街賣工作輔導之外,也提供身障者共同居住的空間,每人皆有獨立房間,建立起自立生活的共居模式。陳安宗補充,鐵皮屋場地空曠,「所以我們在這個地基上設計這些房間,讓輪椅族群進出特別方便。」
 陳安宗分享創辦新巨輪協會十多年來的歷程,走過拆遷危機、被誤認是詐騙集團,他始終堅持讓身障者透過街賣擁有自立生活的能力。 圖/林莉庭攝
陳安宗分享創辦新巨輪協會十多年來的歷程,走過拆遷危機、被誤認是詐騙集團,他始終堅持讓身障者透過街賣擁有自立生活的能力。 圖/林莉庭攝為協助身障者與房東溝通,脊損基金會也推動「脊善之家」,洪心平說:「脊善之家強調是我把房子租給你,你要有自立生活的能力。」他認為,基金會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身障者和房東的橋梁,基金會招募友善房東提供房屋空間,並統一代租代管,選擇有適當動線的房屋,再將房屋轉租給身障者。對於許多房東會希望身障者搬離時,將扶手、斜坡等無障礙設施拆除,洪心平提出的解決方法是,當有身障者搬出,基金會再媒合下一位身障者進來,讓無障礙房子可以繼續運轉。
洪心平說明,在租屋市場中,通常沒有時間化解房東對身障者的特定印象,但房東具有是否出租的選擇權,一旦房東對身障者有所疑慮,則時常傾向不租房屋給身障者。例如使用輪椅可能磨傷地板等擔憂,便會導致房東不願讓身障者承租房屋。為了降低房東疑慮,洪心平說:「基金會用我們的公信力去擔保,我保證你收得到房租。」房東只需收取房租,而脊善之家提供轉介,化解身障者在尋找租屋時屢遭拒絕的困境。
「對房東來說最擔心的不是身心障礙者,不是歧視身心障礙者,他是擔心他的房子會壞掉。」洪心平解釋,因此脊善之家會幫房東和身障者雙方投保保險,降低意外風險。他也補充,脊損基金會希望建立起固定模式,未來希望與政府合作,將服務擴大到全台。
連結社區情感,自立生活的一大步
身障者選擇在社區生活,最主要的考量是渴望與人接觸,當身障者被納入社交網絡,原先不善交際的性格便能產生轉變。陳安宗分享,有些新巨輪協會的身障者過去在家中缺少聊天對象,但他們經由街賣能逐漸適應社會生活,也不再感到孤單,「對阿伯他們來講,跟人打招呼、微笑,都已經可以去克服心裡的靦腆、自卑。」 」全場四十幾個信徒全部躲到遠處,只留下潘家齊與其他工作人員。「其實我很怕,但是我是現場最不能怕的那個,大家都知道我是乩童欸,鬼來了我還怕,那這邊怎麼辦。」後來媽祖發現這女生身上共跟了十三個鬼,為解決問題,便降駕藉潘家齊的乩身驅除怪戾之氣。
這是在混障家屋火災後去幫忙時,邊幫志文擦拭他的物品,他邊告訴我的話。在聽到的當下,心裡是很觸動的,志文一直以來渴望能與人接觸,即使他明白迎面而來的會是不耐或冷漠,仍選擇踏入陌生的人群,對我來說好勇敢,好希望更多人知道,身障者也是編織社交網絡的一環,而別再認為身障者應送入機構或待在家中,當我望見他們真誠、渴盼進入社會的眼神,我好希望更多身障朋友與我們一同生活,能與朋友相約出外遊玩,也能在心煩時出外透氣。周志文也認為,在社區中生活最主要的優點是,身障者能透過與人互動的過程建立自信心,逐漸增進與人交流、應對的能力,也時常收到暖心的關懷與幫助。談及先前混障家屋發生火災後,附近住戶的反應,周志文對一戶從事按摩工作的住戶印象深刻,「我在前門遇到,他們衝過來抱著我問:『你怎麼了?你有沒有什麼事情?』我整個就超感動的。」後續他也收到其他住戶給予的鼓勵與慰問。
身為周志文的照顧者,時常前來混障家屋的邱晧庭則說:「我覺得這裡(混障家屋附近)本身有一個強的在地社區感。」像是鄰居下雨時會主動幫忙收衣服,也有多間店家會免費替周志文剪髮,或者當他與周志文一同吃飯,店家會不收取他的飯錢,「有點打破我對都市的想像,這種氣氛跟鄉下比較像,至少我自己在台北大都市,快十年我沒有感受到。」
 算障團的混障家屋位於士林的整合式住宅,一出門可遇左鄰右舍,離商家近、生活機能佳,身障者除了彼此互助,也能融入社區生活。 圖/林莉庭攝
算障團的混障家屋位於士林的整合式住宅,一出門可遇左鄰右舍,離商家近、生活機能佳,身障者除了彼此互助,也能融入社區生活。 圖/林莉庭攝住所對外動線規劃不完善,也是阻礙身障者與人接觸的原因。邱晧庭觀察到許多安養中心位在公寓某一層樓,若缺乏電梯供身障者通行,他們便無法順利進出,只能終日待在住所,仍形同生活在機構,差別僅在於規模較小,他說:「就是我好像在社區裡,但我其實跟社區無關,只不過是個小一點的機構在社區裡而已。」
與人接觸是身障者選擇進入社區生活的初衷,身障者離開家庭或安置機構後,邁入陌生的社會、一步步重新學習社交技巧,但現今社區大多不具緊密的情感連結,使許多身障者缺少與人互動的機會。對此情況,周志文不禁嘆道:「沒有社區感,就變成大監獄跟小監獄而已啊!」
「一般社會大眾是這樣,因為不了解就會有距離,可能就會有異樣的眼神,或覺得是麻煩。」邱晧庭認為,身障者在社區生活屢遭挫折的原因,在於人際互動的問題未獲解決。尋索身障者在社區生活最根本的需求,便是獲得大眾理解,相應才能確保身障者經濟獨立、消解租屋會遭受的歧視,也才得以滿足身障者自立生活的想望。
採訪後記
做這篇專題的三個星期之間,多次因不捨身障者的處境落淚。因為連結到自身經驗,深入訪談的同時也接收到他們的無奈和盼望,將這些感性思緒轉化為報導,期待能促成一些改變,這些改變關乎公共設施,也關乎大眾的認知與眼光。
自小身邊有一位身障者,我深愛他,我知道他承受多少不解、不耐、不信任的眼光,彷彿他的缺陷即概括他本身的價值。他會慣性藏起自己的缺陷,然後擺出倔強也堅強的表情,看在我眼裡,又心疼又不甘,我無法忘卻。
因此在迎向志文疲憊卻仍帶著希望的雙眼時,我多想牽起他的手,跟他說,有那麽一雙手,我牽了二十年,我看盡了他的鬱悶、自卑,也望見他的快樂、自傲,我知道相較於別人,他的生活須承擔多一些不便,年輕時相信他也曾為此絕望,但他還是將三位女兒養大了。他的眼神也疲憊中帶有希望,像志文的眼神一樣,像每一位我遇見的身障者一樣。
還有新巨輪的伯伯們,前前後後總共待了3個多小時,大多時間與安宗伯伯抬槓,聊新巨輪的街賣新構想、伯伯們的健康狀況等,也喝了好幾杯伯伯泡的茶(很好喝!),是很放鬆、愉快的採訪經驗。記得訪到黃昏時分,伯伯那側的窗戶漏出幾道夕陽微光,灑在他的臉龐,我便邊與他對話、邊看著他在陽光映照下閃爍的眼神,耀眼而滄桑,至今難忘。
也要謝謝願意受訪的每位協會人員與身障者,有他們才有這篇報導。希望每位讀完這篇專題的人都能明白,還有一群人確實需要一些設施輔佐才得以行動,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行動需求不能被滿足,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,與社會互動是他們源於內心的想望。並且,不論法規如何修改、設施如何完備,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人心,我多麽期盼更多人願意理解,而後接納。

.jpg)